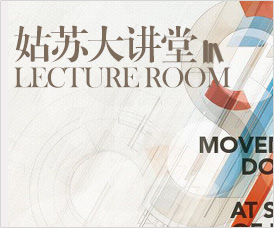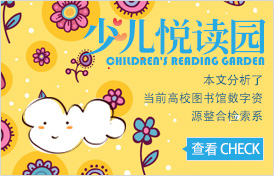我们真的……“来日方长”吗?
时间: 2014-05-29 11:38 稿件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文:李公明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
(法)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著, 蔡鸿滨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
分类号:K835.651
关于自传,阿尔都塞在他这部《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中曾指出,如今任何自传都充满了虚妄不实之词,他认为“这是文学上空前堕落”,并表示自己“只讲实质的东西”(第168页)。对于读者来说,患上“自传警惕症”不是什么坏事,即便是对于阿尔都塞自己的这部自传。
对阿尔都塞来说,他的“实质的东西”与他的写作动机、他对“事实”这个概念的理解、认定和围绕他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舆论有很深的联系。
这部自传包括《来日方长》与《事实》两部文稿,回顾、分析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发展轨迹,尤其突出的是详细而深刻地分析了自己与母亲、妻子百般纠结的情感关系。自传以这位哲学家杀死妻子的经过拉开帷幕,然后讲述了在悲剧发生之后所面对的因“不予起诉”的司法判决所带来的“沉默的墓碑”,进而阐释了写作的根本性动机:这本书是必须作出的答辩,“我这样做别无他求,只是想掀起那块墓碑,把我所掌握的情况告诉每一个人,而不予起诉的程序却要把我终生埋葬在那块墓碑下”(第33页)。但是,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对其动机的解读却认为,“他被宣布不适宜申辩,就是被‘剥夺了哲学家的地位’,而这种最终失去身份认同,这种对再次变得‘不存在’的恐惧,看来就是躲在他的自传背后的驱策力。”(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第124页,林骧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
其实,对“不存在”感到恐惧,这不是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他在自传里究竟是通过为自己辩解而虚构了一个并不真实的人格呢,还是通过故意贬低自己而获得推卸责任的同情?他是真把自己剥得赤裸裸呢,还是以“剥”作为更精心的遮掩?他究竟是否试图让读者感到难堪从而承认他有卢梭那样的勇气,进而获得赞誉?甚至他对女性的欲望,究竟是自然的勃发还是经由欲望意识的投射而自我暗示并刻意强调的呢?说到底,可能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舍弃的追问是:究竟他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他提醒读者:“下面的文字不是日记,不是回忆录,也不是自传。含弃其余的一切,我只想记录一些易于激发的情感所造成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给我的存在打上了印记,并赋予它特有的形式:我就在其中认识自己,而且我想别人也能在其中认识我。”(第34页)这是否预设着对客观真实性质疑的反驳?
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的私隐叙事的真实性问题,我无意探究。但是在“阿尔都塞案例”中,在那块“墓碑”下遮盖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制度的、意识形态的病态故事。他对于“某些暴力形态在我生活中展现的力量”很敏感并努力作出判断,他认为要理解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不可能忽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第35页);因此他声称撰写自传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的问题和“那些或许与我们时代的某些人利害相关的机器”提出质疑和挑战(第34页)。对此,我不认为他是为了减轻个人的罪责而把公众的视线拉向政治的场域。对于我们而言,阿尔都塞所质疑与挑战的那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机器更为庞大、幽暗、更能为所欲为,而公共舆论和民间力量的疾患更多、更无法胜任本应肩负的使命。可想而知,而且事实上已经不断进入人们阅读视线的各种残酷的命运个案,都可以加深我们对阿尔都塞为什么要写这份文本的理解。而更应该引起人们警惕的是,当接触到来自我们悲惨历史深处的类似文本如果明显呈现出精神疾患痕迹的话,或者感到作者自我剖析的真实性存在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耐心和理解能力从中挖掘出的确具有重要精神价值的东西呢?
事实上,阿尔都塞是在清醒和理性的状态中开始这项工作的。1985年3月,当他决定要撰写这部自传之后,马上着手向朋友、媒体征集关于自己的各种资料、线索,“不管是只涉及事实或个人的,还是涉及政治或精神分析的。他的档案保留了为撰写《来日方长》而进行的全部整合工作的痕迹”(法文版编者序)。但是,作者强调“幻觉也是事实”(第86页)。应该区分的是,幻觉作为一种生理事实与幻觉中产生的“事实”内容。
有几个重大的概念一直回响在整部书中。比如“死亡”,“在我童年的头脑里,就这样产生了死亡的威胁”,而他曾长时间地为想到母亲的死亡而惊惶不安,“仿佛我对她的死怀有无意识的欲望似的”(第39页)。又比如“恐惧”,他母亲终身受恐惧症的困扰(第55页),而这对他的成长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我的身体、我的自由,都屈从于我母亲的恐惧症的法律”(第57页)。甚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达到其理论生涯的高峰、出版了《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这两个使他成为最受关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文本的时候,他仍然会感到不由自主的恐惧:“这些文字将使我赤裸裸地出现在最广大的公众面前”,“我生怕招致一场灾难性的公开揭露。”(第155页)与“恐惧”相关联的是“懦弱”:从来没有打过架,没有勇气面对肉体和生死的考验(第137页)。我们不应忘记,与“死亡”、“恐惧”、“懦弱”等概念的缠绕相伴随的是他一生摆脱不了的精神抑郁症。
阿尔都塞强调自己的一生缺乏冒险精神,尽管他非常羡慕勇于冒险的人们。但是,1990年10月25日,德里达在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却强调他的一生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冒险:那些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意味着寻求、试验和付出高昂代价,意味着超乎寻常的激情,“他的冒险是孤独的,不属于任何人”。他的“冒险”首先是思想历程上的,从天主教到黑格尔、到马克思,他的思想探索在不同方向上的积极跳跃,多元性、穿越性和异质性构成思想的冒险特征。其次是在人际关系上的认知、聚合、分离、追求、碰撞,尤其是在母亲的阴影下如何建立自主的认同、如何在与女性的关系中建立爱与被爱的平衡,他正视内心矛盾和不惜一切心理代价追求超越的努力正是情感上的巨大冒险。还有就是在现实政治上他面对庞大、幽暗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器,表现出坚定的疏离和抗争勇气,例如在反对斯大林主义、批评党的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上,坚持孤独的个人抗争。
在阿尔都塞一生中,“爱情”所占据的位置和意义不是孤立的,而是生命体验的核心场域。他认为自己“学会了什么是爱:爱不是采取主动以便对自己不断加码、做出‘夸张’,而是关心他人……不抱任何奢望,不做丝毫强迫。总之就是自由而已”(第293页)。这是很通达的爱情观,但是他在交友中“储备女友”的行为却显得有点阴暗:“只不过为了防止有一天如果我的一个女人意外地离开我,或者是万一死去,我落得独自一人,手边连一个女人也没有。”阿尔都塞希望在极度强烈、充满情欲的感情高峰中去体验与女性的实际关系,因此他会“添枝加叶”地让感情不断加码,让自己相信自己真的在爱,来补偿对女性的胆大妄为和内心不安;同时还以想象的女人形象来维持这种不断加码的激情(第161页)。显然这是一种病态的偏执。
他说生活毕竟还可以是美好的,虽然青春不再,但他终于感到了爱,感到从未如此年轻,“即便一切都快结束了”;最后他说“毕竟来日方长”(第293页)。那么,无论在青春情感上,还是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我们真的“来日方长”吗?
上一条:霍布斯鲍姆谈20世纪文化的衰落 下一条:名门家族史:该谁写,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