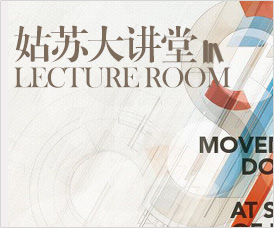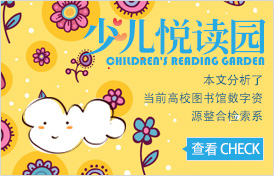口述历史:当想象遭遇现实
时间: 2014-05-17 13:39 稿件来源: 凤凰网读书

文/《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李鸿谷
文字里的人物,一步步走来、伸出手,说道:“我就是周海婴。”然后,彼此落座,讲述与倾听开始……嗯,我们会拥有一次奇妙的回忆与追寻,并得到一个新版本的故事吗?
想象落地。这是我重读李菁文章最直接的感受。
所谓采访,于记者,是有准备的一种职业行为。而之于被采访者,比如周海婴、周有光、黄永玉……著名久矣。文字以及影像制造出的他们,早是我们未谋面的熟人了。只是,当想象里的“熟人”走进现实,伸出手与你相握的那一瞬--想象遭遇现实之际,你将如何?
李菁的兴趣是历史的人物,她的基本操作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至亲或好友,进行深度的采访,然后以“口述”的方式来完成她的历史故事。
“口述”,你说我记,看起来是最容易的一种文章模式。果真?没那么容易。
当双方彼此坐下来,开始共同的追寻旅程,记者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对自己想象的克制与调整--如果采访是一个有智力含量,值得分解并被分析的职业行为,那么,这个技术动作,由准备开始。任何一个普通的采访都需要准备,遑论深度的访问;真问题不是准备,而是你精心准备之后,必然形成了对当事人的想象。准备越充分,想象越完备,在一两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采访里,你的想象是否可能被坐在面前那个活生生的当事人改变?
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当事人有无足够的能量来改变你的想象;只是,克制自己的想象,建立作为倾听者的零度情感状态,才是基本职业伦理。这不是拒绝对讲述者情感的关切,而是警惕来自自身想象的偏见。那个老头黄永玉在讲述比他更老的老头时,所隐藏的情感强度,肉眼亦可洞穿;当他转身讲述自己时,情感会扭曲现实场吗?77岁的周海婴,穿越70年回忆童年时的自己与父亲鲁迅--这个更愿意称父亲为“鲁迅”,而不是“爸爸”的儿子与回忆者--他故事里的那个自己与父亲,是曾经童年的记忆里的,还是经过70多年修正的结果呢?
所谓“口述”,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它的挑战了吧!彼此面对面之际,作为倾听者与记录者的记者,在克服了自己的想象后,迅速地、无可逃避地要面对被采访者的自我想象。
在想象中穿行的这份职业,如何抵达事实的彼岸?
李菁所有卓越文章的起点,是她有罕见的对珍珠般细节的发现与辨识能力:“对我父亲(鲁迅)而言,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吸烟不是放在嘴里,而经常点着了放在那儿烧,既然烧,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候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我们要知道,所有想象都是以一种概念或者标签打结,但在这种闪亮的细节面前,鲁迅许广平爱情婚姻的标签,将如秋叶般无声无息的坠落,生活的本来面目也因此而一览无遗。
被采访者所有建构性的概念化的叙述,将被那些无法作为“证据”安放进逻辑里的小细节给自然瓦解,丰富的非概念性的人生与命运、“新版本”的故事由此诞生。只是,谁能发现这种种真实人生的细节?李菁能。
这种越越性的能力,使李菁在讲述与倾听开始之际,作为倾听者,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既穿越自己的想象与偏见,亦洞穿当事人抑恶扬善的自我标签化。这是一个优美无比的、让想象落地的过程。更多的阅读之后,复盘讨论李菁采访的这个技术动作,我们终能欣赏她的无可复制。
李菁何以如此?或许她对人生际遇尤其转折时候的好奇,更深刻的情怀来自于她对命运的悲悯--“忽见(张)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这虽然是李菁转摘自黄永玉的描述,但她对细节的选择,却实在精当。“隐去”之时,命运固然苍凉;但隔着遥远的时空,这份苍凉被有心人重新择出,人生亦因此而温暖。
那些走出文字里的人物,经过李菁,想象落地,再次形成文字、形成这本书。它当然迥异于你曾经印象里的那些人物,而且不可替代。
上一条:名门家族史:该谁写,如何写? 下一条:评何顿《来生再见》:这群抵抗者被后世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