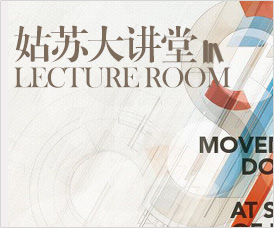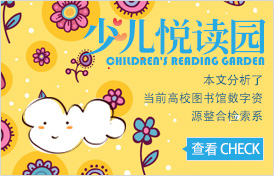他为灵魂生存 ——《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
时间: 2015-06-23 09:09 稿件来源: 光明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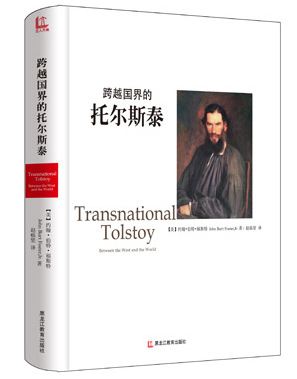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个多世纪以前,《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问世并广泛赢得了经典叙事体的声誉。在某些地方,这两部小说被尊为文学巨著的绝对标准。以今天更广的文化背景看,许多读者会理解它们显然是世界文学的典范。不管世界文学的意思是指应以母语表现价值的作品,或仅以翻译给读者以印象的作品,再或是对其他文化开放,为跨语言、民族或传统障碍而培育理解的作品,托尔斯泰的这两部小说均为名不虚传的杰作。
《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写于作者自1910年逝世一百周年,旨在尽可能更广地拓展我们从他作品中汲取的观点。即使此书对他创作的性质和意义或许能产生新的影响,但其宗旨仍力求说明比较文学对交叉文化探求的益处,以期对世界文学运动做出贡献。很显然,托尔斯泰在这双重领域里都是中枢人物。他先以一种强烈的,但并非无条件的西欧归属感写小说,这联系着老式的国际主义比较研究模式,之后他寻求代以一种预示和挑战我们今日全球视野更广阔的世界观。在我们当前的跨越国界时期,不仅文化内而且跨地理文化区域都发生着文化流动,托尔斯泰介于西方和世界的事业为这更广的文学空间的出现和发展特色提供了更多的思考。
在歌德《有择的亲和》中,当奥提丽惊人的权威宣称“没有比艺术更能使人回避社会和依附社会”时,她第一次使用的“世界”一词唤醒了纯属温文社会的世态。但是她第二次用的代词所指却转向了一个大艺术家更广阔的视野,一个寻求超越此时此地的,可称为跨越国界的视野。这些广阔的抱负在此前的格言中已有所指:“即使最伟大的人也联系着生活中曾有过的脆弱时刻”(《有择的亲和》)。其意为,正是以这种间接方式,这些人物的伟大才体现了他们是超越自己时代的,同样,也造就他们在世上的特殊地位,因而超越了国界。
超国界转向了我们今天居住的更大、文化更多样的新民族世界,它有着对欧洲之外更广大区域文化的认识以及超国界的更高层交流—总之,一个曾是后殖民、全球化并且常是多语种的世界。在《比较文学的挑战》中,美籍西班牙比较学者克劳迪欧•奎林(Claudio Guillén)对这一领域超前的概述,已开始向这个方向转移。他的书是根据他在西班牙和中国的讲学而写的。这两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都严重受阻,直接排斥国际态度。奎林强调,学术要寻求超出本国丰富文化的文学绝对公正,“出发点不是本国文学,也不是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相反,基本动力应该来自对超越本国文学观的“渴望”,他以塞万提斯为例,着重说:“眼光只看到本国圈子的伟大作家是少见的。”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奎林来说,在他领域转向的相对早期,首选的词是“超民族”,一个比超国界含义更高远、更宁静但都市化的词。
当托尔斯泰开始明确地考虑世界文学以及偶尔发现他的作品有益于影响这些思想时,他便开始引起西方外部的注意。本书谈到他对来自印度和埃及两位此类作家的超国界影响,同时将评估与托尔斯泰接触时的几次对话,并参照和分析他的作品。在那些以欣赏态度或从他的例子脱颖而出写作的小说中,这些对话可能采取好评的观点。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作家在托尔斯泰级别的先驱身上发现的意义都会对他的价值和成就局限提供有益的洞见。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 (1880-1936年)和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哈福兹 (1911-2006年)在这方面很突出,因为这些西方之外作者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纠正托尔斯泰作为“西方”本质作家的形象。
托尔斯泰本人曾在《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1897)一书中提到过“世界文学”一词。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解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将其与俄国之外的作者与作品联系在一起,包括司汤达、福楼拜、歌德、普鲁斯特、兰佩杜萨、马哈福兹等。作者在文中选用的跨文化读物环环相扣,联系紧密,从十九世纪的德、法、意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二战危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文学视野的发展。他着重分析了托尔斯泰一直引发国际共鸣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举世瞩目的小说。
在《哈吉•穆拉德》这部小说中,与《战争与和平》相反的是和平时期的浪漫须让位给战争。这两部小说表现的是既作为历史事实的自身权利,又更广阔地作为托尔斯泰反复作祟的道德感重复的转义比喻。很合适地,最后一个形象的叙述场景出现在俄国与开垦田野中长着“摧毁了的蓟”的中东交界处。小说以俄国土地连接“鞑靼”外人,这便设定了生活似谜一般局限的喻义基调。这部作品以强大的交叉文化幅度扩大了《伊凡•伊里奇之死》和《主与仆》的故土世界。它确实是跨越国界的托尔斯泰最终合适的一词。
上一条:不再蒙昧:人类历史上的启蒙之光 下一条:王德威:爱在蚊疫蔓延时